李亚群宇
李亚群晨
李亚群庚
李亚群霓
李亚群芳
李亚群晴
李亚群萍
李亚群焜
李亚群睿
李亚群茉
李亚群菲
李亚群云
李亚群贺
李亚群柳
李亚群龙
李亚群琳
李亚群亭
李亚群蕊
李亚群鸿
李亚群悦
李亚群丹
李亚群红
李亚群逸
李亚群静
李亚群峰
李亚群露
李亚群玉
李亚群炫
李亚群玳
李亚群玮
李亚群艳
李亚群琳
李亚群燕
李亚群娟
李亚群祯
李亚群誉
李亚群玎
李亚群岩
李亚群芊
1938年,日寇开始对中国抗战大后方进行大规模空袭。成都是日机重点轰炸的城市之一,逼迫许多市民不得不到郊外去寻找临时避难所。李劼人原本没有自己的房产,早年居住在状元街外婆家,后又相继在指挥街、斌升街、桂花巷租房居住,《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等作品就是在桂花巷完成的。1939年春,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李劼人从老友谢苍璃手中买下了东门外沙河堡的菱角堰边的两亩土地(今在锦江区内),盖起了几间简易的疏散房,李劼人为这一简易住所题了“菱窠”二字,意为“菱角堰边的窠巢”。后来由我国著名书法家谢无量先生专门书写了“菱窠”一扁挂在门楣上。
菱窠当时地处偏僻乡间,建筑十分简陋。土墙草顶,坐北朝南,宽阶沿,共计三间房:东为客厅,西是卧室,中间作为书房。草屋虽是躲避轰炸的陋室,但对已经48岁的李劼人来说则是一件大事。他说:“几间茅草房比较简陋,但对我李家来说,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因为自我八世祖入川定居以来,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搬一次家东西失散不少,特别是书籍。我有房子后,可以不再担心我在数十年置备的几千本中国书籍和积存的报纸、杂志散失了。”菱窠最初的生活条件虽然差,但却是作家李劼人寻找到的一块难得的清静宝地,所以他格外看重这个居所,曾用笔名“菱乐”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从1939年春举家搬入后,到1962年逝世,李劼人一直生活、创作在这里。
李劼人在菱窠的23年中,曾多次对菱窠进行维修和改、扩建。抗战胜利后,李劼人将草屋改建成两层楼房,并添了附属房。屋顶尽管仍是麦草,但整个风格却是中西合璧:“明一柱”式的宽阔阶沿在室外形成一圈回廊。这是李劼人精心设计的,显示出他对建筑艺术极高的审美品位。菱窠原本没有围墙,后来菱角堰边长起了不少铁藜,李劼人便将就铁藜、柳树等圈成了一道篱笆墙。在院墙内种了柳树、桃树、竹子和花卉,还开辟了小菜园,俨然一幅乡村田园的景色。
1959年,李劼人用《死水微澜》、《暴风雨前》的稿费,对菱窠再次进行了大修,将房顶上的麦草换成了小青瓦,土墙换成了砖墙;鉴于乡下小偷猖獗,篱笆墙早已挡不住他们的“进攻”,于是又预支了部分《大波》的稿费来修围墙。这样,篱笆墙也改成了红砖墙,菱窠由此形成了真正独立的院落,从而为1998年的大规模修葺奠定了基本格局。
菱窠不仅是李劼人创作的“世外桃源”,也曾是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的避难所。在上个世纪40年代,李劼人利用菱窠的偏僻之利,掩护了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洪钟因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逮捕,曾在菱窠住过;赵铭彝也在菱窠躲过好大一阵,直到在川东找到职业掩护后才离开;著名作家陈翔鹤则先后两次在菱窠避难。第一次是1947年5月,陈翔鹤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提出欲到菱窠躲风头,李劼人不假思索就表示:“欢迎,欢迎,就住我这里,吃住都没有问题……”第二次是在同年夏末,陈翔鹤再次上了黑名单,被地下党紧急安排到菱窠,后为了安全起见,李劼人又将陈翔鹤转移到乐山嘉乐纸厂任驻厂秘书,一直到成都解放才回来。
特务们也曾多次到菱窠搜查,却从来没有捡到便宜。有次,一伙特务在菱窠翻箱倒柜,搞得一片狼藉,这下惹恼了李劼人,只见他捞起长袍的前摆,揶揄地问特务:“我这儿还有个胯胯,你们还搜不搜?”令特务毫无办法。
李劼人的骨头历来就“硬”,早年他写杂文,笔锋就敢直指当权者。不料居住在菱窠,却常常遭到乡间保长的敲诈。国民党胡宗南部溃退成都时,有一天,李劼人又被保长叫住:“李先生,这是派给你的一千斤草料,请过目。”李劼人接过单子一看,上面写的竟然是“李劫人”,李劼人顿时讥讽道:“保长,我是李劼人,不是李劫人呀!”保长见写错了字,马上赔个笑脸:“字写错了改过来就是了嘛!”李劼人说:“我才错了!你上个月派一千斤,这个月又派一千斤,我哪来那么多钱?这样派款法只怕真要逼到我去‘劫人’了!”说完扬长而去。
李劼人历来就十分爱好整洁,中学时代得了“精公”的雅号。所以在菱窠,打扫卫生就成了件大事,丝毫不能马虎。每天清早,老保姆吴嫂一起床就上下忙开了;李夫人早晨的第一件事也是打扫房间。楼上楼下家具很多,但每天都先要用湿帕子全部抹上一遍,然后还要用旧绸子再擦一遍,因为菱窠在堰塘边,空气潮湿,用绸子擦过,家具才会发光。最难整理的是李劼人的房间。书报杂志太多,书柜顶上,床头柜上都是书;还有纸笔墨砚以及尚待回复的书信等,都放得整整齐齐的;书桌上还经常摆着插有野花的小花瓶和一些瓷人儿、瓷狗儿之类的小玩艺儿。稍不留心,就会把书房搞乱,因此打扫书房总是由李夫人亲手去做。
李劼人写作是很勤奋也是很辛苦的,早饭过后,他就开始工作,经常都要熬到深夜,菱窠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通电,夜晚伴随老作家的只有一盏豆大的菜油灯。万籁寂静的菱窠,除了偶尔听见几声狗叫,便只有从昏暗的油灯下传出来的翻书声。在菱窠的23年中,李劼人创作了矛头直指“四大家族”的长篇小说《天魔舞》,写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说成都》,编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好人家》,修改了《死水微澜》、《大波》,还翻译了好几部法国中、长篇小说……
通常,李劼人在菱窠的生活,或创作,或写信,或进城上班,或与来客交谈,包括乡间的农民朋友。李劼人在菱窠曾先后接待过巴金、叶圣陶、沙汀、艾芜、伍非白、戴执礼、桑原武夫等中外著名作家和学者;还与张秀熟、李亚群、张东生、段可情、林如稷等文艺界的领导与同行在菱窠研讨过四川文艺的发展大事。在菱窠,李劼人还时常接受《文汇报》、《成都晚报》记者的采访和出版社的造访。1962年11月12日,作家出版社韦君宜等三人在菱窠向李劼人约稿,李劼人在这里谈了他的创作打算:《大波》第四部准备在1963年脱稿,“下一部的计划已经考虑得比较具体化了,准备写“五·四”时代各种各类知识分子的动态,定名为《急湍之下》”,在这之前将先写一部中篇历史小说《张献忠》,之后便写国民党统治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写到解放为止。他说“我计划写到85岁。”然而老天不长眼,就在这次谈话一个月之后的12月24日,李劼人就不幸与世长辞了,他留在世上的最后声音:“我那《大波》还有30万字呀!”便成了文学史上的一道绝响,也成了菱窠的一个永久的遗憾。
20世纪60年代,菱窠发生的另一个故事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侧影。李劼人的女儿李眉女士曾回忆李劼人捉贼的故事,说来颇有意思。
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居民每月定粮只有10.5千克(21市斤),为了让家人的肚子里能增加点油水,李劼人利用居住乡间的条件,养了一头猪,十只鸡,还有几只兔和鸭。在那个全国绝大多数人都在挨饿的年代,这可是一笔了不得的巨额财富呀!于是菱窠成了人们眼红的去处,多次招来梁上君子“打起发”(指起偷窃的念头)。1961年春夏的一个深夜,李劼人临睡前去上厕所,院子里树影摇曳,光线暗淡,李劼人刚走进厕所,不料门后猛然闪出一道黑影。李劼人本能地一抓,正好抓住那人的衣襟,俩人立即扭成了一团,年过古稀的李劼人凭手指间感觉,那是个年轻人,完全能够将自己一掌打翻,却不知怎的,对手却反将他牢牢抓住。早已气喘吁吁的李劼人只急得大喊:“抓贼娃子呀!”喊声惊动了家人,李夫人首先冲了进来,见人影扭倒在地,上前便掰住像丈夫那人的手,不停地叫道:“快松手,快松手!”李劼人情不自禁将手松开,那贼娃子趁机翻身就溜了。回到房间,李劼人非常遗憾没有看清贼娃子的脸,于是乎埋怨夫人怎么不去抓贼娃子反倒来抓自己人,李夫人却十分心疼地说:“你呀,都七老八十啦还抓贼,要是他给你一刀怎么办?”全家人好一阵苦笑。副市长家进了贼娃子,当然非同一般,于是成都市公安局专门派了人牵起警犬来侦查,案子却始终没有告破。李劼人对此并不在意,却反倒替那个逃脱了的不速之客担起心来:“那个贼娃子咋连我都打不赢呢?大概是没吃的,太饿了吧!”
老作家菱窠抓贼,这大概也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有趣的事吧。
? (待续)
本文来自作者[海雁]投稿,不代表千泰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m1.hr8848.cn/zlan/202508-2076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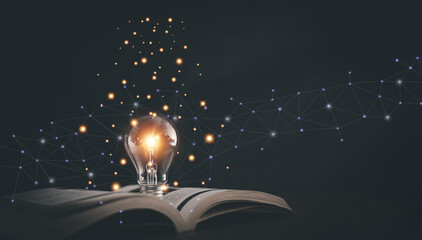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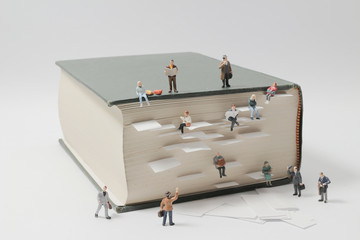

评论列表(3条)
我是千泰号的签约作者“海雁”
本文概览:李亚群宇李亚群晨李亚群庚李亚群霓李亚群芳李亚群晴李亚群萍李亚群焜李亚群睿李亚群茉李亚群菲李亚群云李亚群贺李亚群柳李亚群龙李亚群琳李亚群亭李亚群蕊李亚群鸿李亚群悦李亚群丹李亚群红...
文章不错《名字大全女孩姓李亚群》内容很有帮助